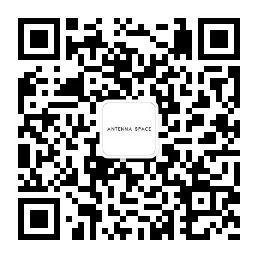2024-11-16
Owen的作品源于他对世界的观察,在流动的视觉状态中带着真诚、幽默、古怪和诗意。如今,Owen Fu已从艺术市场上的一个名字,变成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个体, 一个在创作中不断探索的艺术家。借由本次艺术刊第五期“艺术穿越 Art Across”的契机,SuperELLE将我们所认识的Owen Fu缓缓道来。
2024-11-16
Owen的作品源于他对世界的观察,在流动的视觉状态中带着真诚、幽默、古怪和诗意。如今,Owen Fu已从艺术市场上的一个名字,变成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个体, 一个在创作中不断探索的艺术家。借由本次艺术刊第五期“艺术穿越 Art Across”的契机,SuperELLE将我们所认识的Owen Fu缓缓道来。
2025-4-23
Rappelant l’étrangeté hypnotique des films de David Lynch, les mini-toiles d’Alexandra Noel révèlent une imbrication subtile entre mémoire et imagerie numérique. (仅限于法文版本)
2025-05
Li’s work speaks to a specifically Chinese context, the one-child-policy generation’s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family, amplified by the recent pandemic’s enforced separations. (only English Version)
与谈者:
主持:贺潇
嘉宾:王伊芙玲韬程、程心怡、李绮敏(Christina Li)
展览标题中的“影子”和“亮面”,对应着两位艺术家对各自的创作理念真诚的交流与剖析,“怎样表现”与“为什么表现”,贯穿于艺术创作历史看似对立的两重要素,通过绘画的转译和单纯的并置,传达出一种交互共鸣的精神场域。
两位艺术家与策展人李绮敏、艺术写作者贺潇,在展览开幕当天展开对谈,围绕着各自的离散生活经历、美术教育知识谱系、绘画实践中背景及尺幅的处理方式等议题,意识流般的叙事交汇在不被知觉的某处。
李泳翔作为旅行作家 / 艺术家,有一种近乎考古学家的耐心,将二维平面的绘画完整置入建筑、声音的暧昧的声场中,造就极具渗透性的艺术实践。但正如上文所述,这并非对绘画本身的反叛,也不是对媒介革新的简单附庸。李泳翔曾坦言,不论是“锈色”中构筑的厅堂,还是旅行后记,都是精心编辑的成果,他并不否认在创作的层面对记忆和历史时空进行的人为加工。不过,本次李泳翔在地理与创作意义上进行的双重的“黑色旅行”所抵达的最终地带,或许正是历史建构中的人为性与脆弱性。
2024-12-26
正如卡尔维诺的“月球的距离”在李爽滞留欧洲期间带给她的很多安慰,此次荣宅的个展也为它的观众们带来慰藉,在无声的情动时刻,轻抚那些难以言说的裂痕。
2024-11-27
正如卡尔维诺的“月球的距离”在李爽滞留欧洲期间带给她的很多安慰,此次荣宅的个展也为它的观众们带来慰藉,在无声的情动时刻,轻抚那些难以言说的裂痕。
2024-10-08
This autumn, Lee will take over the vast space of Tate Modern’s Turbine Hall, having been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Tate Hyundai Commission. She tells me the work evokes miners’ changing rooms and is “really for people — for people to enjoy and just be around.” Lee’s been reading Michael Taussig’s My Cocaine Museum (2004) while preparing the exhibition, which is about the lure of the forbidden and how we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Modeled on the Gold Museum in Colombia’s central bank, it is a parody aimed at the museum’s failure to acknowledge the enslaved Africans who mined the country’s wealth for almost four hundred years, engaging with the essence and inner life of heat, rain, stone, and swamp, as well as with the sublime fetishes of evil beauty. Li — who is Tate’s curator of international art — underlines that Lee’s work “invites disorientation,” which then “slowly dissipates into a sense of intimacy, empathy, belonging, and hope… without following a fixed script.” As the youngest artist to ever be awarded the Commission, not only does Lee’s daring work flip the script, it rearranges letters, rips up the page, and it’s not hard to imagine the artist then unashamedly feeding it to the dog bit by bit.
2024-05-20
A new videowork by Liu Chuang, full of allegory and representation, posits an alien invasion against the beauty and lost opportunities of Earth and its dumb inhabitants.
2024-春
无论是从高原湖泊中提取锂元素的蒸发池和被迫迁徙的生物,抑或是在丝绸之路上缄默前行的僧侣,刘窗的创作都围绕危机驱动、时局变化中的地缘流动性展开。这些分布在地图各处的点位,就如同振翅的蛾子和地铁内手机设备的低振,看似毫无关联,却在百转千回中以微弱的连接共生。
2024-春
在城市和历史中往复漫游的近十年里,崔洁的视觉系统逐步成熟。身边的城市街景反复更新,更新反复推进、停滞,而她通过绘画,检阅城市以及在其中的人类生活与其他生态:改革开放时期的高楼建筑和城市雕塑、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居住设施、现代家庭生活方案以及上海本地动植物在不同空间中的历史交换。从穿越都市街头的主观视角,到对二手材料的物质媒介的考察调研,崔洁绘制出西方现代发展模板套用在中国现实时产生的无声龃龉与暴烈冲突,把错置的时间感折入几经覆盖、反复擦拭的画面叠层中。
2024-01-08
如此听凭事态发展的态度,绝非消极的投降,而是将偶像崇拜视作一种发现新世界的体验,同时也赋予了直觉力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特权——这种笃信让无边无际的地平线破除了局限感。正如李爽所说,作品在为她指明去处。
2024-06-19
面对科技乐观主义应允的光明未来,和随时宣称要取代人类的AI,忧虑之际,我们低头看见了自己的双手。
我好像从未在一个艺术展览上读到过如此丰富的作品展签。在上海天线空间先前呈现的英法艺术家组合丹尼尔·杜瓦和格雷戈里·吉奎尔 (Daniel Dewar & Grégory Gicquel) 的展览“纬织经辐”中,敞亮的大厅宽松地摆放着三、两件橡木雕塑,墙上挂着的绣织物和橡木浮雕都沉浸在从高挑的天花板上的排灯散射出的接近自然色调的光线中。再走近墙上的织物,在我只能词穷地找到“毛毛虫”去描绘眼前所见的情况下,艺术家给出了这样的描述,织物上绣着的准确来说是:蚯蚓、蜣螂幼虫、野大麦草、紫羊茅草、罂粟花、草甸羊茅、英式黑麦草、朱砂蛾幼虫、大天蚕蛾幼虫、豹灯蛾、鬼脸天蛾幼虫、醋栗尺蛾、大天蚕蛾、鬼脸天蛾、朱砂蛾、麻雀和竖笛……
这个囊括了从土壤深层的昆虫到地表植物、飞虫和地上人类遗留物的清单,被两位艺术家有序地刺绣在亚麻布上,让我们看到位于布面底部的蚯蚓,各种蜿蜒的姿态似乎正在湿热的土壤中蠕动;大天蚕蛾幼虫肥嘟嘟的躯体在画面中层奋力前行,大片朱砂蛾从上至下排列成美丽的图案,悄悄遮盖住混迹其间的鬼脸天蛾有点凶哒哒的外表,罂粟花、草甸羊茅穿插其间,还有不知哪位园丁忘记在地上的竖笛……
杜瓦和吉奎尔以一种植物学家的严谨态度竭尽写实再现的“百草园和昆虫世界”,似乎遵循着某种物种分类的原则,在填充了薄棉的百衲被一样的亚麻布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包含着从植物、昆虫到棒球帽、锁边缝纫机等等不同物种、不同类别的物品勃勃共生的生态系统。当然,这里貌似植物学大典的排序方式,与开创现代分类学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 (Carl von pLinné) 创造的自然系统分类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毕竟,林奈创造的分类学,无论体系如何庞大丰富,针对的首先是对植物王国的混乱局面做出井然有序的管制,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极端理性主义在自然科学的投射。而两位当代艺术家创作的出发点,立足在艺术、人文、自然与科学相交汇的奇点。那些经他们亲手打磨、拼接的自然天成和人工合成的物件,散放着艺术性的精神光晕,表现出实用性的返璞归真。
过去20余年来,丹尼尔·杜瓦和格雷戈里·吉奎尔这对相遇在大学时代的艺术合作二人组,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主导当代艺术愈趋观念化的主流中,走出一条回归传统雕塑、民间工艺、乃至通过普遍通用的艺术材料,重启实用主义与装饰艺术的独特路径。2012年,他们成为法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奖项——杜尚奖的获奖者,评委点评的关键词不出意料地落在了传统工艺和文化传承上,赞誉他们创作中用重复性劳动,手工性和装饰性拓宽了固有的审美传统。
时代真的是变了呀!1917年,当为这个大奖命名的马赛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把从他纽约居所楼下的五金店里买来的一只陶瓷小便池签上R Mutt的名字,以“泉”之名投放到当年的艺术沙龙的时候,一个关于何为艺术的提问成为占据二战之后的艺术界一个持续讨论的母题。杜尚对于现代艺术革命性的贡献,包括对于作品与现成品,作者权与所属权,艺术家之手与艺术家之选的争辩,在艺术风向的潮涨潮汐中,依旧保持先锋。在观念艺术大行其道的上世纪60、70年代,艺术家的想法几乎享有着高于作品生产的地位,在日趋政治化的观念艺术语境中,留给艺术生产中手工性和技术性,美学体验与实用功能的讨论空间并不多。回顾一下英国艺术家迈克尔·克雷格·马丁把一杯放在玻璃隔板上的水杯标注为“一颗橡树” (1975年) 的著名的观念艺术作品,创造艺术的思考在马丁的逻辑中成为一场物质命名的转换,而有关作品创作工艺的点则落在了如何优雅地在空间摆放物品上。时间到了21世纪,艺术世界的自我反省激烈地参与到人类如何与这个星球的不同类物种共生的命题,被消费主义社会破坏的自然环境、不均衡的资源分配、气候变化的威胁、超级技术发展的忧患等等当代人面对的日常问题,成为当代艺术参与和做出反应的领域。
源自古希腊的“technē” (技术) 一词,原本包含“艺术、技艺” (art, craft) 的涵义。在被大数据、人工智能塑造的高科技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技术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转换为流水线上精准成型的模板,被赋予光洁可人的平滑外表。编码控制的工具理性,代表了现代技术对世界精准和一致的塑造能力,相似的想法被反复传播和深化,遂成真理,很快,就连汽车都只需压膜出厂了。面对科技乐观主义应允的光明未来,和随时宣称要取代人类的AI,忧虑之际,我们低头看见了自己的双手。
在人类发展史中,是手指功能的进化让第一个智人在2百万年前灵活地用手举起一块石头,敲击另一块石头,制造出锋利的石器,从而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来到今日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改变地球生命史的关头,重提人类的手工技艺和自然材料等前现代话题,提醒我们重审自身文化与自然文化长期被忽略的不对称关系。在拉图尔 (Bruno Latour) 的理论体系中,现代人在自然面前的盲目文化自信,可能就是现代文明自我崩溃的内部结构,所以,拉图尔发出警告:我们从未现代过。重塑人与非人,自然与文化的与关系,帮助我们在气候变化威胁下的地球找到着陆点。在当代艺术领域,重访原始文化、部落文明的展览已经形成趋势。看看正在进行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从北极的萨米人,到太平洋的毛利人纷纷为各自国家做代言人,织物、纤维、竹子、木板等传统西方艺术史中缺席的材料获得高度重视,可以说在这个“处处都是外人”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主题之下,与少数族裔、女性、动物等等获得关注和解放的话题中,也包括处在艺术世界边缘的手工技艺。
展览对应的英文标题“the weaver and the spoke”, 描述的是篮子编织中使用的两种纵横股线,与中文标题“纬织经辐”回应的中国古代的织造技术,都是农耕时代的人类劳作和技术的体现。在织造工艺中,一团白纱经纬穿梭可以变为一卷素绢,在杜瓦和吉奎尔的艺术理念中,重复劳动对于物体形状和功能的改变,也带来以物为核心的多重对话。展览中呈现的以针织衫为主题的手工雕刻橡木浮雕,在水平或垂直流动的木纹上呈现横向与纵向的针法,对于谙熟女红的观众,一定有许多值得仔细推敲的针法,只是这巨大的木头毛衣没有可以被穿出去的场合。观众被邀请观看一个毛衣的雕刻,但也是在看一个雕刻的毛衣。
在两位艺术家的词汇表中,似乎不存在艺术性与实用性孰高孰低的纠结。《带编织乐福鞋和腿的橡木柜》是一个坚实的橡木打造的柜橱和柜橱上立着的一个穿编织鞋的人的小腿的木雕。镶嵌篮子浮雕的柜橱三面都可以打开,里面就是一个大容量的储物橡木柜。至于站在柜顶的小腿在做什么,我们就又要回到何为艺术的本质提问了。
在杜瓦和吉奎尔这里,重要的不是给出答案。从作品空降到上海的展览空间那一刻起,橡木柜、木毛衣,以及被艺术家从花园里带到织物上的菜粉蝶幼虫、花椰菜……一同构成了这个兴旺的生态圈中热闹无声的对话。看到织物上的花椰菜,我不禁想到林奈晚年,在自己执教和生活的乌普萨拉大学植物园里耕作时的一句感叹:当我从泥土中挖出今天要上桌的花椰菜,它圆形的外表让我想到了祖先的头颅,分解在脚下泥土中滋养的何止是花椰菜……物种来自共生,万物皆为一体。如哈曼 (Graham Harman) 所言:是共生导致了对象的诞生,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共生形成新的对象。在杜瓦和吉奎尔的世界里,有许多这样的共生。
Stanislava Kovalcikova的画作令人心神不宁、躁动不安。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真实的,描绘了取自后现代生活的主题:压力、心理健康、流动的性行为。”然而,在绘画中,展示这些状态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些情况下,语言大多是失败的。这不是一种批评,只是一种观察,”艺术家表示。为什么她把展览称为她的小巨石阵?为什么精神之事务很重要?为什么一切的一切都是绘画?
2022
某种程度上说,带有拟人元素的形象是Owen Fu绘画中的“情绪动物”或“心兽”,它们并非一早就排好队等待着被绘画和被观看,而是潜藏在大把对艺术家与观者而言都并非异质的时间里,一如徘徊在日暮时分丢失了主人的影子。当然,与它们的交谈甚至亲密也是可能的:如果你也恰好足够空虚。在与这些心兽的相处中,Owen Fu以形形色色的线条作为私语或交谈的句法。在Owen Fu的小尺幅绘画中,一盏台灯、一个花瓶、一把茶壶会在炭笔线条下变成某种安谧或狡黠的化身——这些线条从造型角度而言无意构筑任何具象之物,但情感的质变恰巧发生于“无目的”与“非准确”之中:画家以试水的心态抛出飞钓之线,那些被绘画的对象是先跃出记忆或心智的水面,才落定在画布之上的。这些上钩的“愿者”,亦是艺术家真实生活中的种种局部。而语言总是有限:经过时间的积淀与流淌,有些经历和反应变得模糊,有些差错出现在画面的时候刚好成为情感的另一重解,从而对艺术家原初的情感体验作了推进。
公众号名称:天线空间ANTENNASPACE